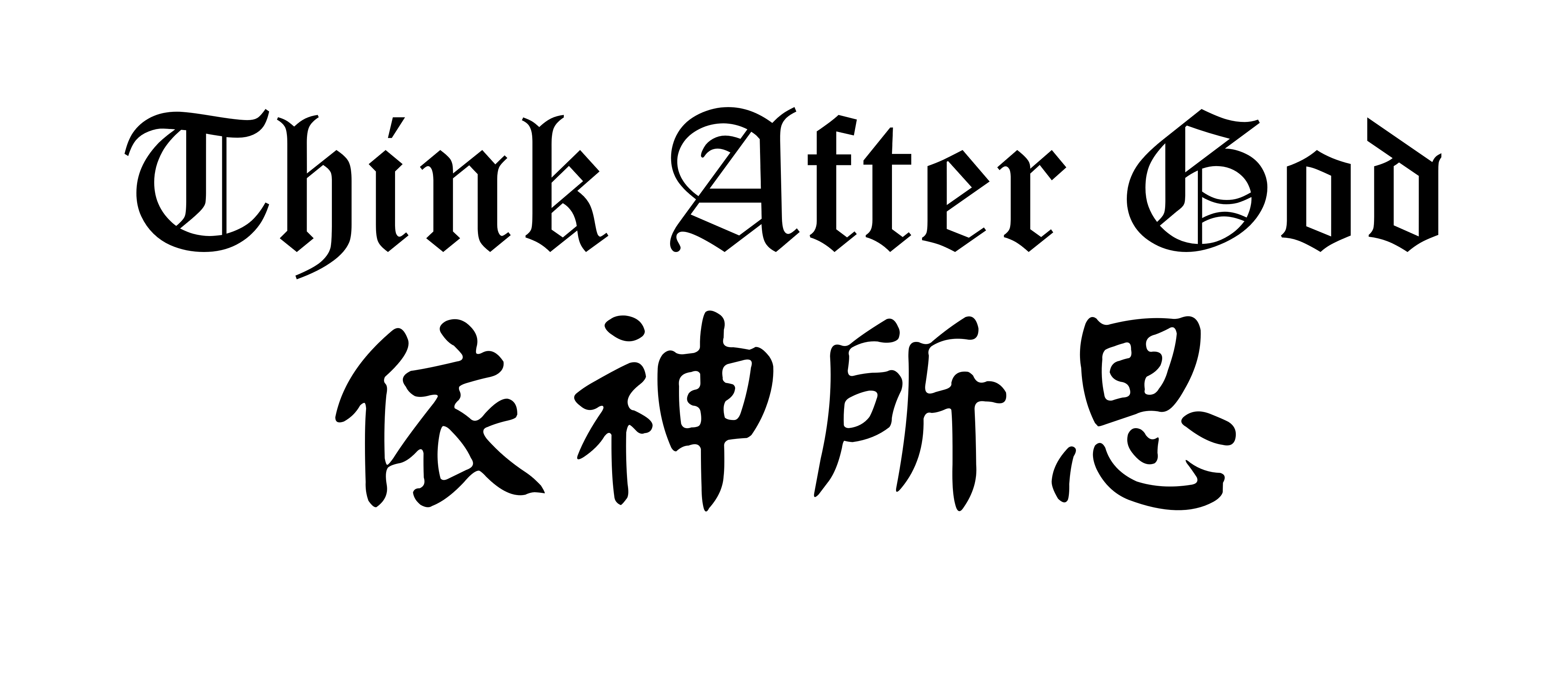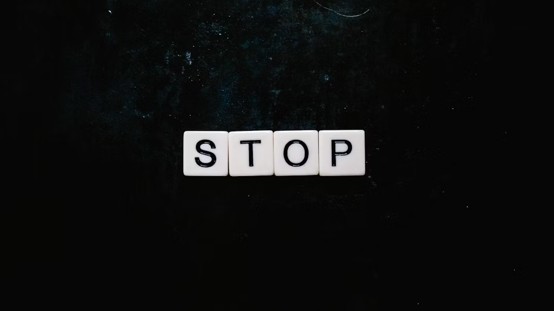下面约翰开始阐释与神相交的内涵和意义,第一句讲的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是光,这当然是用光这个被造物作为类比,如同主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门”、“我是葡萄树”(约6:48, 10:9, 15:1)。在圣经以及在其他场合,“光”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实指,即可见的光,或者是自然光、或者是人造光;其二是代指、类比,用光代指、类比其他。
把神明与光联系起来是人类宗教普世的现象。苏美尔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玛雅人等敬拜光,如太阳、月亮、星辰、闪电;佛教讲佛光、开光;波斯的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有光明之神;人造的光,如火、灯也被直接敬拜或者用于宗教表达。既然异教也讲光、光之神,那圣经讲“神是光”、“我是世界的光”(约1:4, 9, 8:12, 9:5, 12:35-36, 提前6:16, 雅1:17, 启21:23, 22:5),与异教有什么区别?异教的寺庙道观里有灯,耶和华的帐幕、圣殿里也有灯,有什么区别?“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类似的话在异教也有啊?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提前6:16),异教的有些神明似乎也是如此啊?
圣经教导与异教的区别有很多,最基本的当然是圣经启示的是自有永有的独一真神,异教的神是被造物或者被放大的被造物。所以,异教讲的光明和神明,不可避免的会把光以某种形式神化,自然的光是异教敬拜的对象,拜日、拜月、拜火,人造的光也被赋予神奇的意义,有些是神明的所在,有些是与神明沟通的途径,如萨满教的火或灯、佛教的香烛,有些则关系到个体或者群体的命运。异教的光是被神化的光,有着超越光本身的特殊意义和功能。
属神信仰运用关于光的各种符号,始终清晰表明这些符号的被造物属性(创1:2-5),不论是普遍的光,还是具体的太阳、月亮、星辰、闪电、火光、灯光。圣经讲“神是光”,主是“出于雅各的星”、“公义的日头”、“明亮的晨星”(民24:17, 玛4:2, 启22:16),但圣经从来没有说“光是神”、“太阳是神”、“晨星是神”;帐幕和圣殿里有灯、有火,但帐幕和圣殿里没有一个物件是神,约柜的基路伯不是神,其上的施恩座是空的(出37:1-9)。帐幕圣殿的灯、火本身没有能力,就连约柜本身也没有能力,以色列人抬着约柜与异教作战,约柜本身并不保证他们取胜(撒上4:1-11,神之后惩罚非利士人也不是因为约柜本身)。新约设定的敬拜,连帐幕、圣殿的这些仪式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些?因为异教、迷信的阴魂不散。使徒教会和紧接的初代教会没有关于日、月、灯、火的迷信,因为圣经的教导清楚明确,刚从异教剥离的基督徒也非常警惕。直到三世纪、四世纪,多位教会领袖和多次教会决议禁止将蜡烛作为非照明的用途。但随着教会的社会化,异教化也随之而来,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异教对于日、月、灯、火的迷信进入教会,并积重难返。例如,教会把异教纪念太阳神的日期,改为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接近一年白昼最短的日子,白昼自此开始变长;月亮是天主教赋予马利亚的重要符号;教会开始按照旧约帐幕的模式进行敬拜,蜡烛自然也作为祭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甚至对蜡烛的配方有明确要求(这显然不是作为照明功能)。
今天多数基督徒没有直接敬拜日、月、灯、火,可不少基督徒受到天主教以及过往异教的影响,对光有着异教式的迷信,最普遍的是蜡烛。今天绝大多数教会已经无需蜡烛作为照明,但为什么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在聚会时故意使用蜡烛?因为别人告诉他、因为他告诉自己,这很属灵,很有与神同在的亲密感、有神圣的氛围、有让人投入的感觉。这是什么?这是迷信,蜡烛作为一个物体根本不具备这些功能,根本不具备介入新约敬拜实质的能力,什么实质?新约的敬拜是在真理和圣灵里的敬拜(约4:23),只有神的话语、神的灵可以,蜡烛不可以,什么物件都不可以。神是光,这并不赋予光任何神圣的意义;主是葡萄树,也不赋予葡萄任何神圣的意义,就像主是门,没有赋予门任何神圣的意义。异教的迷信始终在寻找各种时机渗透教会,同时有些基督徒颇好此道,乐此不疲,这是使徒说的,“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西2:22-23)
人类另一普世的现象,是用光明、黑暗作为类比、代指,讲的不是物理上的光明和黑暗,而是非实体的、抽象的意义,讲的是神明、生死、善恶、好坏等等宗教、道德、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他们对光明和黑暗的基本指代也是一致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把光明看作正面的,黑暗看作负面的:光明意味着生,黑暗意味着死;光明意味着善,黑暗意味着恶;光明是天堂、神明之所,黑暗是地狱、鬼魂之所;光明意味着进步,黑暗意味着落后;光明意味着解放,黑暗意味着压迫;光明意味着快乐,黑暗意味着痛苦;光明意味着胜利,黑暗意味着失败;光明意味着希望,黑暗意味着恐怖;光明意味着安全,黑暗意味着危险。这个共识不仅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即使在日常沟通时也有,无需过多解释,每个人都知道“光明的新社会”、“黑暗的旧社会”在表达什么,某某被比作“如初升的太阳”是在表达什么,某某被形容为“暗无天日”是在讲什么。想到在暗夜中的一盏明灯,每个人的感受是本能的。
那为什么人类对光明和黑暗有如此共识?是因为光明和黑暗本身携带这些属性吗?当然不是,光明和黑暗是被造物,在起初美好的创造中,既有光明又有黑暗(创1:31)。光明和黑暗不具备道德属性,本身没有生与死、好与坏、善与恶、进步与落后。那人类为什么会赋予光明和黑暗宗教、道德、社会、伦理的属性?因为人类需要一个最为简单直接的符号,来表达世界最为简单直接的现象。什么是世界最为简单直接的现象?是有生有死、有善有恶、有真有伪、有天堂有地狱、有快乐有痛苦、有进步有落后、有希望有恐怖、有胜利有失败、有安全有危险。这些对比是真实存在、每个人真实感受的。正因为这些正反对比的普遍存在,而且它们都是抽象的概念,但又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必须思考和沟通的概念,所以人需要寻找一个直观的自然现象进行表述,哪个自然现象?最为简单直接的表述符号就是光明与黑暗,不是大小、长短、冷热、快慢,是光明与黑暗,无需解释的直观感受,连初生的婴儿都可以感受。
因此,光明与黑暗的这些指代,成为人类解读世界、理解世界的一部分,包括对生与死、真与伪、善与恶、苦与乐、进与退、胜与败的解读。神作为万有的创造者、掌管者、启示者,在神的话语中也运用光明和黑暗进行类似的指代,圣经讲的是关于神的、属灵的、属神生命的、道德的、伦理的属性。那圣经和异教在这一点上有什么区别?
异教通过光明和黑暗表达的对世界的解读,是典型的二元分化、二元调和、或二元对立的解读,如中国古代的阴与阳,阴阳始终存在、始终是被造世界的一部分,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成了世间万物。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也是类似,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始终共存。近代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辨证学说,根本上也是这个对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对抗(或调和)。异教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把生死、真伪、善恶的对比,看作与光明和黑暗同样的正常、自然。对异教而言,光明与黑暗是普世的、正常的,生死、真伪、善恶也是普世的、正常的,因为人类目光所及之处,有光就有暗,有生就有死,有真就有伪,有善就有恶,有进步就有落后,有成功就有失败。异教只能观察到自然,必然把观察到的一切自然化,既然存在、就是合理,既然合理、就会永存。在异教,有光就有暗,有光明之神就有黑暗之神,有掌管生的神就有掌管死的神,有良善的神就有邪恶的神,他看到的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他认为一切最终也都是二元对立的,包括神在内。他不可能有别的结论,也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希望。如果二元对立是自然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存在,也是恒久的存在,生死、善恶、真伪只是人的区分而已,同时,人类也永远停留在这个困境,始终是有生有死、有善有恶、有真有伪,没有尽头。
圣经启示的真神不是如此,“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的光明和黑暗是类比,在讲神的神性,什么神性?在神,有生而无死,有善而无恶,有真而无伪,神是一切美好、良善、圣洁、公义、恩典的源泉,在他没有邪恶、没有犯罪、没有污秽、没有瑕疵。这样的神不是人通过观察被造世界可以推理得到的,因为被造世界看到的都是二元对立。只有神启示给我们,我们才可能知道,光明和黑暗是起初神创造的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死亡不是、邪恶不是、虚伪不是、压迫不是、痛苦不是、哀伤不是;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看到的二元对立背后不是神明的二元对立。神是独一的,且是完全的美好、良善、圣洁、公义、恩慈、生命,只有神是如此的神,我们才不会永恒的陷入生死、善恶、真伪的二元世界,生死、善恶、真伪的永久循环。
所以,圣经讲“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没有胜过光”(约1:5, 和合本表述不确),“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彼前2:9),圣经讲的不是物理的光明与黑暗,讲的是生死、善恶、真伪、自由与奴役、希望与绝望、天堂与地狱,看似和异教的概念相同,实际上,只有独一真神有资格这么讲,只有神子耶稣基督可以这么讲。作为人,观察到世界存在生死、善恶、真伪是远远不够的,把这些现象科学化、哲学化、宗教化也是没有意义的,世人几千年来所做的就是如此的努力,也是如此的徒劳。人以为人参透了,可殊不知他的认知是完全错乱的,混淆了正常与非正常,自然与非自然,当然也混淆了神与被造物。罪人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人间的宗教、哲学、科学,是神的启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