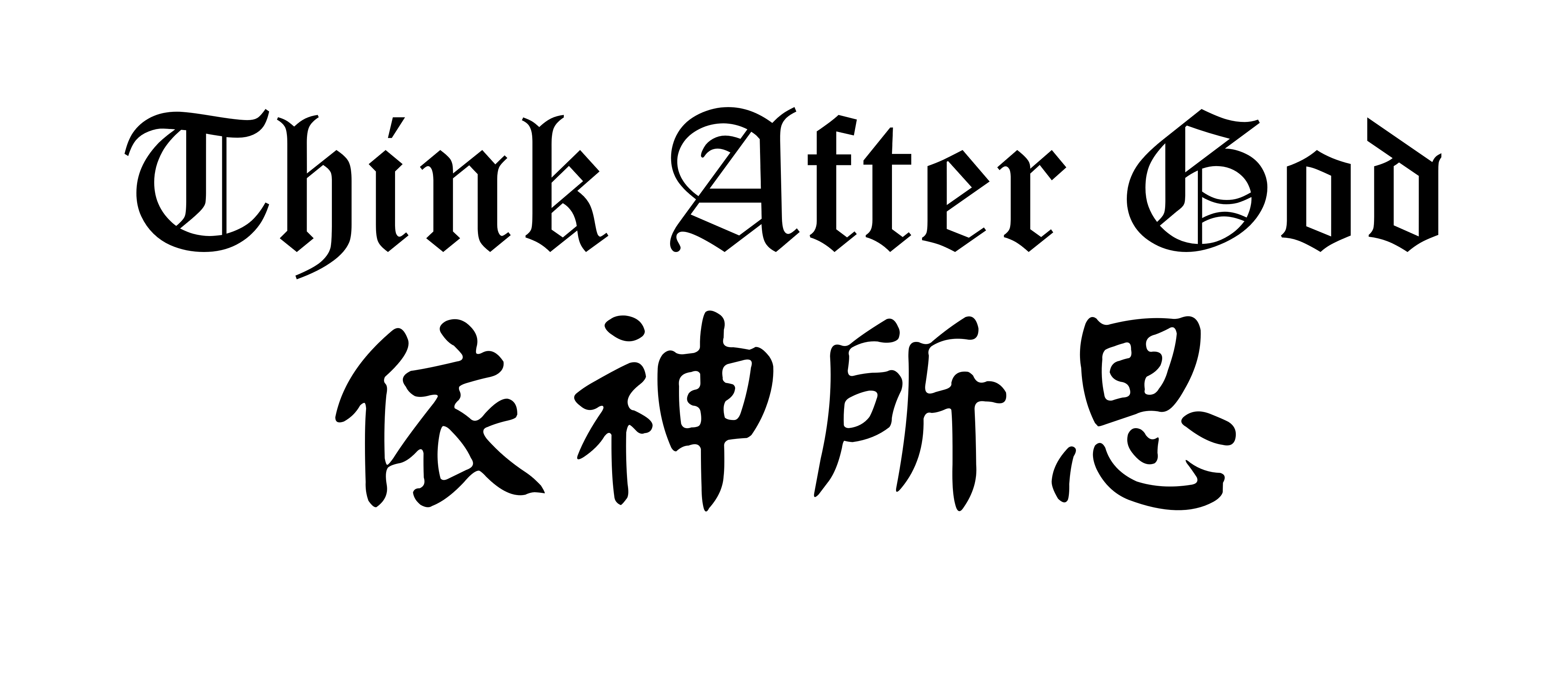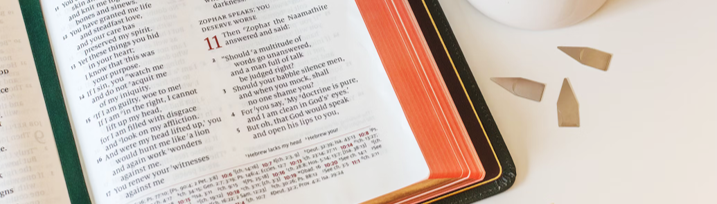约翰-佩顿(John Gibson Paton, 1824-1907)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传教士,出生于苏格兰,他常年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今天的瓦努阿图)传教。自1858年起,约翰-佩顿先是在塔纳岛(食人部落),除了他的家人,他还带着几位附近岛屿已经信主的原住民。他们在其中经历了诸多患难、饥饿、艰苦、死亡的威胁,几位家人因病去世,传讲福音的工作持续面对很大阻力,原住民的传教士被杀。后来他到附近的阿尼瓦岛继续传讲福音、翻译圣经、照料病人、收养孤儿、建立学校、发放药品,教当地人使用工具,当地居民慢慢的接受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完成了从食人族到基督徒的转变,在当时多数人看来不可能的转变。他的事工影响和激励了澳大利亚、苏格兰等地更多传教士来到南太平洋,到1899年,他翻译的阿尼瓦语新约圣经交付印刷,传教士已经在当地三十个岛屿的二十五个展开工作。今天的瓦努阿图,有超过90%的居民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佩顿的回忆录(John G. Paton Missionary to the New Hebrides, An Autobiography. Edited by his brother),是他晚年对他的家庭、成长、教育、传教事工的回顾,是神的恩典的荣耀见证,也是属神生命信靠、敬虔、舍己的见证,诸多细节感人至深。下面是其中的一段节选,提及他的父亲以及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版本,New York, Robert Carter & Brothers, 530 Broadway;翻译时有删节,斜体字为译者标注)。
————————————————————————————————
从很早开始,我们每个人(指约翰–佩顿的弟兄姐妹,共11人)都认为与父亲一起去邓弗里斯的教会,不是惩罚,而是快乐;四英里的路程对我们而言是一种享受,除了路上的风景,有时我们还能看到市镇生活的新奇事物。其他敬虔的基督徒,也从同一个教区到邓弗里斯(当时教区的官方教会很差)参加敬拜,这些敬畏神的农民一路同行,我们这些年少的可以从中看到基督徒生命应有的状态。他们去教会的时候,充满期待,他们的灵魂憧憬着神;他们离开教会时,渴望着交流他们听到和领受的关于生命的教导。信仰呈现给我们的是认知的新鲜感,但这并没有排斥属灵的渴望,反而在激发属灵的渴望。父辈关于信仰的交谈是真挚的,不是伪装的,是出自他们生命的,这吸引着我们聆听他们的交谈。
我们在主日晚上有特别的阅读圣经时间,母亲、孩子们、客人轮流阅读,并提问、回答、解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神的慈爱、神在救主耶稣基督里的丰盛恩典。我们定期学习教义问答,包括问题、答案、以及圣经相关经文。有些人可能说,教导儿童这些教义问答,只会让他们更加远离信仰。我以及周围人的经历与之恰恰相反,这帮助我们建立了信仰生命的基石。我们长大之后,的确会对其中的教导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我们没有一个觉得这对少年是无用的。当然,如果父母不是敬虔、真挚、充满感情的,如果他们只忙于事务,或者更有甚者,他们虚假和伪善,那这些教育对孩子的结果当然会大有不同。我还记得那些主日的晚上,圣洁、快乐的时光,基督徒的父亲、母亲与孩子们一起度过;我也记得父亲来回踱步,给母亲说今天讲道的主要内容。……他会让我们回忆讲道提到的一些主题,并嘉许我们做听道的笔记;他也会自然的提到圣经的故事或者殉道者的事迹,以及《天路历程》里的典故。我们好像比赛一样,每个人轮流大声朗读,其他人聆听,父亲在某些地方做一些补充,其他人也要把各自认为的重点写下来。我们十一个人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没有一个觉得主日枯燥、让人疲倦,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缺乏的。有些家庭让孩子们做这些事情,是依靠强制,而不是依靠爱;求神帮助这些家庭。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也可以视作信仰的一部分。如果有需要严肃管教的事情,他会先到房间祷告,我们知道他是把这件事情放在神面前。我觉得这本身可能是最严重的惩罚,如果仅仅是身体的惩罚,我可以对抗;可父亲的祷告,是神在打动我的良知。我们由此更爱父亲,因为我们看到这在他心里是多么沉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十一个人动手,我们遵从父亲是出于爱,而非恐惧。
(下面一段是他前往格拉斯哥面试一个奖学金的机会,他要首先步行40英里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格拉斯哥。)
我的父亲陪我走了开始的六英里。他在路上的教诲、眼泪、嘱托,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仿佛昨日。每次回想起来,我还是会流下眼泪。最后的半英里左右,我们几乎没有说话,父亲和往常一样,手里拿着帽子,他的头发披散着。他一直在默默的为我祷告,当我们偶尔对视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泪簌簌的落下来,我们都没有开口。到了分别的地点,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有大约一分钟的沉默,然后严肃但深沉的说,“我的孩子,愿神祝福你;你父亲的神赐福你,保守你脱离凶恶!”
他说不出别的话,只是默默的继续为我祷告;我们流着泪拥抱,分别。我尽可能快的跑,当在路的转角处,我觉得他就快要看不见我的时候,我一回头,他还站在那里。我挥着帽子向他告别,过了转角,离开了他的视线。可我心里仿佛被什么堵住,其中的酸楚让我无法继续,我冲到路边大哭起来。然后,我小心的爬上河堰,看他是否还站在那里,我瞥见他也在往河堰上爬,看我走到了哪里。他没有看到我,往我走的方向呆呆的凝视了一段时间,他下去了,往家的方向走。他的头上还是没有戴帽子,我知道,他的心里还在为我祷告。我的眼泪迷蒙了眼睛,直到他的身影从我的泪眼中消失。我继续赶路,我在心底里立下誓言:求神的帮助,我立志今后行事为人一定不能让这样的父母伤心或蒙羞。
我们分别时父亲的样子,他的嘱托、祷告、眼泪,他站在路上、爬上河堰、慢慢离开,他没有戴着帽子的背影,这一切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即便是现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它们如同刚刚发生。当我后来遇到许多试探,他离去时的样子保守着我。我可以说,因着神的恩典,这让我不随从周围的罪恶,也是我学习时的动力;就学业而言,我不想让他失望,就我的基督徒生命而言,我要效法他的榜样。
(下一段与他的父亲无关,在这里翻译出来,以提供一个当时传教的剪影。其背景是:一位原住民传教士,纳姆里,被当地部落劫持,佩顿刚把他带回。佩顿称他为“教师”。)
他(原住民传教士纳姆里)急迫的想要再回到那些人中间去。我(佩顿)请求他暂留在传教士的住所,这样更为安全,我们也更为放心,但他说,“先生,当我看到他们想要流我的血,我就想到传教士初次来到我的岛上的时候,我那时也想杀他,就像他们今天想杀我。如果那位传教士就此离开,我将继续是异教徒;但他来了,不仅来了,还继续在我们中间教导,直到因着神的恩典,我改变了,成为我现在的样子。现在那位重生我的神,同样可以改变这些塔纳人,让他们爱神、事奉神。我不能离开他们,我会在传教士的居所休息,但白天我要回去,把他们带给耶稣。”
我意识到,他有这样的责任和动力,我无法阻止他。他又回到他的村庄工作,之后几周事情看似有所好转。当地人对我们没有原来那么敌视,不再那么惧怕异教巫师的威胁。但是,一天早晨在敬拜的时候,纳姆里在跪着祷告,这时那个野蛮的巫师冲过来用棍棒打他,他倒在地上流着血、没有意识。其他人逃跑了,把他一个人放在那里。他清醒一点之后,慢慢的爬到传教士的住所,这时临近中午,他已经不能再坚持。我看到他,急忙跑过去,他对我说,“先生,我要死了,他们也要杀你,你快逃离。”我坐在他旁边,安慰他,帮他擦拭伤口。他很坦然,向上仰望耶稣,因为即将看到主的荣耀而喜乐。他的痛苦是巨大的,但他安静的忍受,他不断的说,“因着基督!为了基督!”他持续的为逼迫他的祷告,“主耶稣,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要把你的仆人们从这里带走,不要把你的信仰和敬拜从这个黑暗的岛屿带走。神啊,让所有塔纳人都爱耶稣、追随耶稣!”
对于他,耶稣是一切,一切的一切。他带着主荣耀的确据离开了我们。在世人看来,他是卑微的,但我知道,这是在主里事奉的伟大的圣徒,他将加入主的殉道者的荣耀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