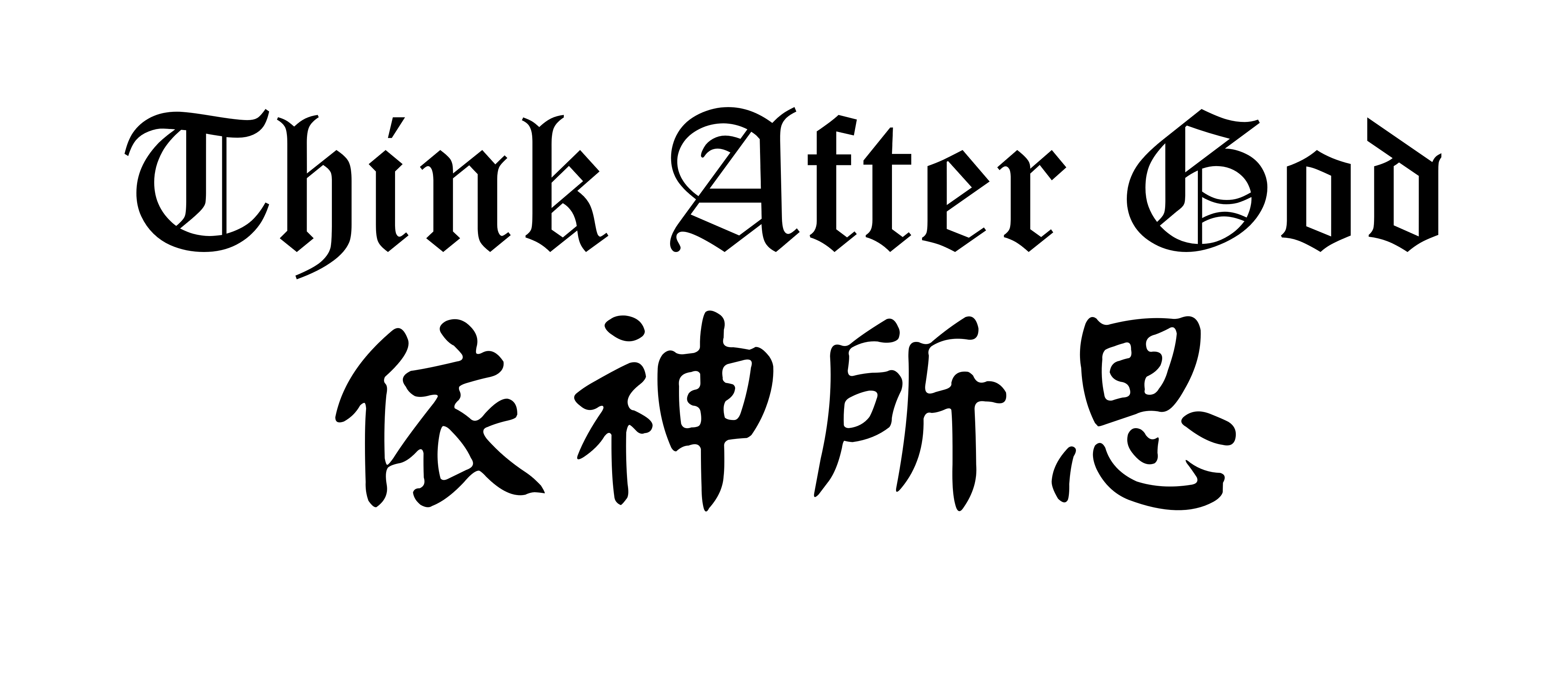道教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吗?的确,属神信仰与诸多异教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所谈的内容、所运用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致的,都会谈到神、终极、理想、善恶、真伪、拯救、幸福等等概念,不少的异教也会涉及与属神信仰类似的定义,例如认为神是某种终极、超越的存在,认为人应当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些形式上的相似并不能掩盖二者在实质上的区别,即二者在思维认知体系、在所理解的宇宙秩序、存在体系的根本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是宏观架构,而且一定会渗透并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例如对何为神、何为善恶、何为幸福的认识。
二者的根本区别,首先是,属神体系是基于自有永有的神的创造和掌管,基于神的启示,属神体系对一切的理解,包括对神、对世界、对人,对一切道德准则、被造物关系、神人关系的理解,都是基于这个真实的神,真实的启示,真实的工作。这个神不是一个虚幻的神的概念,而是在创世以前自有永有,并按照己意创造世界、掌管世界、并审判万有的神。异教可以有神的概念,而且有很多种神的概念,但没有一个异教的神祗如同真神,甚至没有可能接近。异教体系虽然可以用诸多宗教语汇、哲学构造,但异教体系是基于被造物的自有永有,基于人的存在认知从神的独立,不是从一般的神的概念中的独立,而是从自有永有的独一真神的独立,从神的恩典和启示中的独立。也就是说,所有异教的学说,对宇宙、世界、人类的解释,包括其对神祗的解释,都是在否定独一真神的前提下、在独立于神的过程中进行的。异教学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神的反叛,因为他的前提是:人可以离开真神和真神的启示去追求、探索,并且最终明白何为神、何为人、何为信仰,这本身就是人类狂妄的表现、是人类在罪中疯狂的自信。其学说的假定是,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在堕落的世界,在被罪扭曲的认知情感体系之下,罪人可以知道神、知道如何敬拜神、知道善恶真伪,这是对神的否定,对神定秩序的否定。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向他,罪人如何能够离开这样的真神,然后继续找到真实、正确、幸福?我们应当透过异教所采用的复杂词汇,探究异教对宇宙、世界、人类的终极解释是什么?这个解释到底是基于自有永有的神、神的工作、神的启示?还是基于被造世界、罪人对被造世界的认知?异教体系基于被造世界的自有永有,意味着其对世界的解释最终只能停留在被造物的层面,不管他用的词汇是神祗、终极的概念、理性、规律、科学、轮回、命运,他还是在用被造世界的元素来组装这些词汇,这是我们分析异教时的重要切入点。
通俗的用法常常称之为道教,但不论是在历史传统还是现代学术中,道家和道教还是有一定的区分。道家一般认为肇始于老子(一说黄帝)、庄子,后来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等也位列道家经典,在后期整理的“诸子”中都有一席之地。道家可以看作是更偏向哲学的一种思想,有宗教意味但总体来说宗教意味不是很浓厚,但始于东汉的道教就是宗教意味很浓、但哲学居于次的学说,结合道家、方术、仙家、五行等元素,又与民间宗教杂糅,形成多个变种。道教是泛神多神教,一炁(气)化三清,三清(三尊神)一般视为最高神祗,但也有其他的神祗体系,发展出天庭、人间、地府等三界,由玉帝统领诸神,这也是泛神教的典型特征,信仰没有定型,只有一个泛泛的概念,而信仰实体可以变化。当然,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道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比体制性的道教广泛、深刻,渗透到政治伦理(例如西汉初流行的黄老)、社会伦理(汉末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传统书画、诗词)等多方面,宋明时代成熟的儒家思想,理学、心学都受到道家的影响(也有佛教)。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谈这些学说的历史沿革,其在历史传承中也有丰富的多样性,即使仅比较老子、庄子,各自理论也有鲜明的个性。下面以老子的道德经[1]为例,仅就一些基本概念,从上述思维体系的角度进行检视。
由于圣经翻译所采用的“道”,尤其在约翰福音,很多人认为圣经中的“道”与老子的“道”是相同的,甚至有些人以为老子谈的就是神的启示、谈的就是基督。这当然是误解,混淆神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无视神的恩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视人的罪性和世界的堕落。这两个文献中的“道”是文字的相同,某种意义的相似,但本质和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圣经启示的“神”与异教谈的“神”不是相同的。下面看老子对“道”的一些解释(原文引用,可参见通俗译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
老子对“道”的定义是,在天地之前就有的混然,永不停息的运转,为万物的根本。这听起来像不像圣经的“道”?像,是不是圣经的“道”?不是!老子的“道”是在天地存在之前的已有的“规律”,是冥冥不可知的规律,是这个规律以某种形式成就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但真正的神是“规律”吗?不是,真正的神是自有永有的人格化的神,规律没有人格、是僵死的,没有意志、是机械的,但自有永有的神是三一的神,有丰富的人格、丰富的意志,而且是自有永有的人格、意志,并且凭己意行万事。万有的存在不是这个“规律”自然运转的结果,而是自有永有的神的主动的决定,人格化的神的有意识的决定。老子在这里的定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定义一个哲学上的终极,但这个终极最终只能是规律、原则,而且是从被造世界推导的规律、原则。老子的“道”看似像真神,其实不过是对被造世界“规律”的放大,成为一个所谓的终极规律、根本规律。后面,老子对这个所谓终极的规律,万有根本的“道”,解释的很清楚,“道法自然”,“道”是终极的吗?看似像是,但其实不是,“道”是自然规律,“道”取法自然,是自然所有的“道”,这个自然不是仅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有的现实,说到底,是什么在解释“道”?是自有永有的世界。看似“道”是终极的,但这个“道”依然是依附于这个自有永有的世界。
老子又是怎么解释“道”的运作?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
看到这些,有些人会认为这里讲的与圣经的创造很契合,圣经不也讲从无到有的创造吗?甚至某些人还用这个去推导三一的神。首先,要明确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圣经讲的是自有永有的神从无到有创造万物,不是虚空的“无”,也不是老子解释的“道”,也不是不可名状的“奇点”(大爆炸),而是源自神的旨意、神的能力,而且是自有永有的三一神,不是在被造世界形成的三一神。老子以及道家运用的“生”,很能反映其学说的内涵,与近现代进化论所谈的“化”、宇宙论所谈的“炸”是一致的,都是被造世界内部的运作、变化,圣经启示神的工作,表达的不是被造世界内部的演化,而是自有永有的神的“创造”。老子这里将一切归于“无”,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当人类希望定义一个纯粹的终极概念时,真正的纯粹只能是“无”,看似是无所不包的,实际是空洞无物的。因为即使是罪人也能理解到,一旦把这个终极固定在某种“有”的形态,必然在限定这个终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没有限定,只能是“无”,而异教定义的“无”只能是虚无的无。所以他的解释最终是“无”,看似玄妙实则荒谬。
这就涉及到在认知论中的矛盾,如果世界的终极,“道”,是这样的存在,那人又怎么可以知道呢?见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状哉?以此。(第21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
这个“道”可知又不可知,恍惚之中有象,有物,有精,而且还很真切,老子的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个“道”,但他对这个“道”的理解却是如此的暧昧,很确定、然又不确定,他的认知始终是蒙昧的,他的确定始终是飘忽的,“道”无为又无不为。这个认知的虚无是所有异教的共同缺陷,他可以非常有信心的宣告自己的发现,但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认识是在混沌之中的片段、碎片化认识。没有基于真神和真神的启示,这是必然的。
老子的社会伦理颇有近代卢梭、黑格尔之风,谈自然、谈辨证,谈自然就意味着不承认世界、人类的堕落,谈辨证就意味着不承认存在绝对的真理、不变的准则,在这些前提下,老子的社会伦理是消极的,即使在中国传统中,也非主流,而是在某些时代暂时的策略、某些人群避世的选择(当然,这不是说儒家或者其他宗教没有避世的理念)。见下: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
虽然在某些层面,老子对罪人的某种趋势是一种批判,但这种对人性、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理解与圣经的教导是相悖的,基督徒不可能认同这种道德观念、善恶观念,对人性,也就包括对人的罪性采取的消极措施,也不能随从今世的人所有的类似理念。这也是异教的普遍问题,它可以意识到某个问题,但他对问题的解读、对问题的解决都是极端的,在处理一个极端问题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时间关系,以上讨论仅提及道家老子的少数概念,但这些概念足以反映其思想的异教特征,以及与属神信仰的根本分歧。
[1] 此处仅谈道德经的内容,不涉及历史文本、文本传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