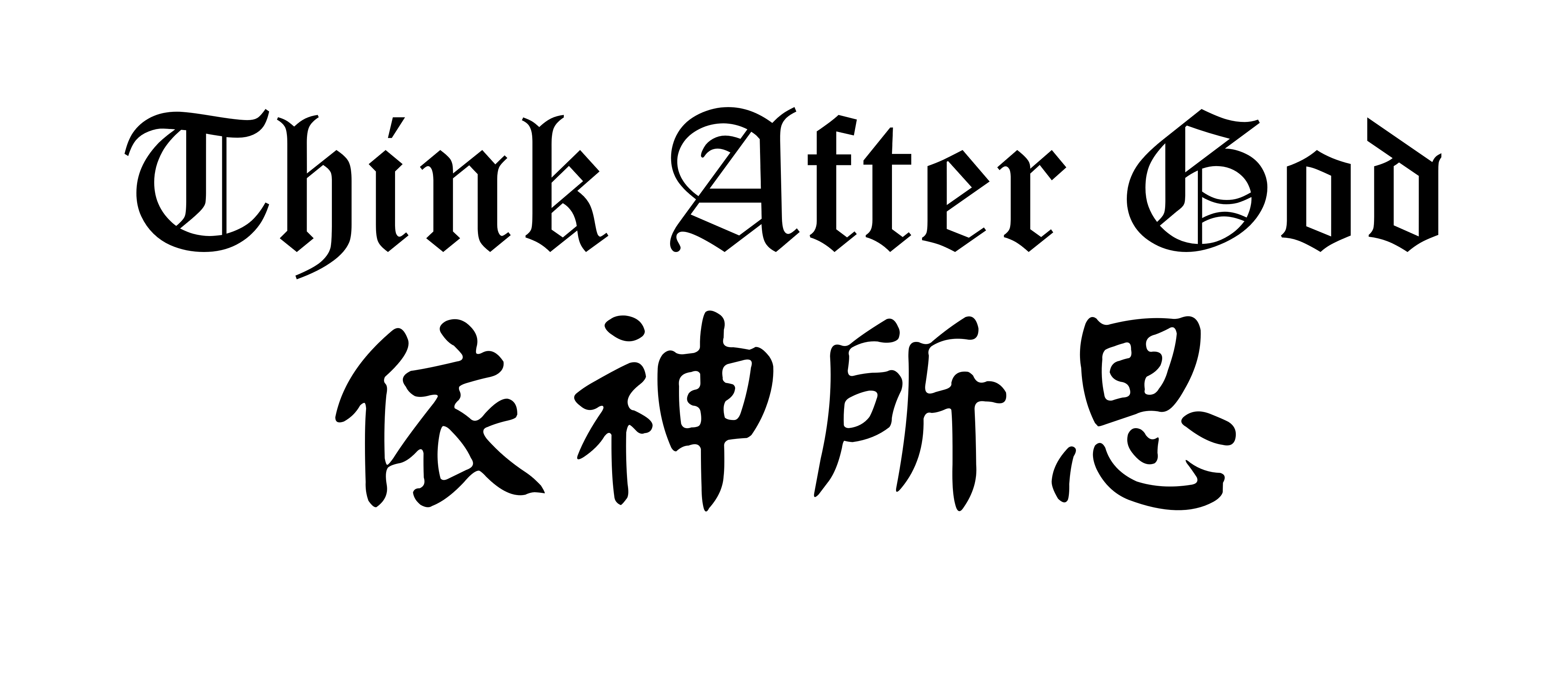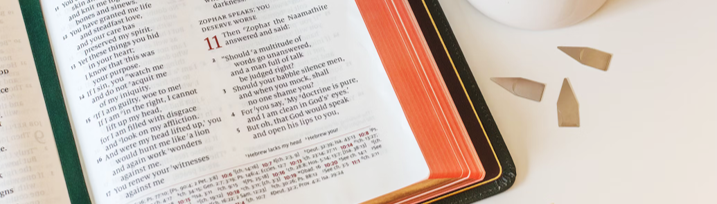罗伯特-维尔肯(Robert Louis Wilken)的《罗马人眼中的基督徒》[1],讨论了初代教会时期非基督徒如何看待基督徒、如何认识基督教。本书主要是通过几位人物:小普林尼(Pliny, 61-c. 113;政府官员、律师、作家)、盖伦(129-c. 216;医生、哲学家)、赛尔修斯(Celsus, 2世纪,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 c. 234- c. 305,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31-363,罗马帝国皇帝,361-363在位)。通过这些人物直接或间接留下的文献,作者结合历史情境以及其他文献,简要但切中要害的诠释了罗马社会的宗教状态,异教对基督教的认识、反应,以及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互动。
上述几位主要人物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也代表了基督教从边缘化的存在,慢慢为异教精英注意和熟悉,最后成为罗马帝国合法宗教、主导宗教的过程。除了呈现这个历史脉络,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异教对于基督教的批评(本书标题的“罗马人”指的是罗马异教徒,精英阶层的异教徒),这是我们下面着重关注的,因为这些批评在今天读起来并不陌生,近现代异教意识形态对基督信仰的批评,与如出一辙。普林尼、盖伦、赛尔修斯、波菲利、尤利安等人讲的,放在卢梭、伏尔泰、斯宾诺沙、叔本华、达尔文、马克思等人口中,放在自由神学的拥趸口中,不会显得突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1:9),的确,近现代异教不过是古代异教的复活和重新包装,而这背后,反映的是属神信仰与异教之间恒久不变的分歧和冲突。
第一章,小普林尼出身罗马贵族[2],在公元117年被任命为罗马庇推尼行省[3]的总督,他给罗马皇帝图拉真[4]关于基督徒的信,几乎每个教会历史的书籍都会提。普林尼的主要职责除了清理庇推尼行省的财务,还有一项是平息当地的政治纷争,其中有间接关于基督徒的,也有直接关于基督徒的。图拉真等罗马皇帝,对于民间社团组织的成立,保有相当怀疑和谨慎的态度(p12);即便是职业行会、民间慈善或自助组织,官方也担心其成为地方政治和帝国政治的不稳定因素[5]。这时的基督教还不为多数罗马精英知晓,普林尼根据自己得到的消息,判断基督教为一种外来的邪教(superstition, 罗已处置了多起外来邪教事件,关于雍正对基督教类似观点,参见文章)。由于基督徒特有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他们不被当地民众所容纳(p24),这对当地民众、对官长而言就是威胁。普林尼自己也承认并没有发现基督徒有什么罪,他的作法是提审被人举报的基督徒,讯问他们是否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说是,就被处决;如果说不是,并当场亵渎基督的名、向异教的神献祭,就可以被释放。对普林尼,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仅仅这个名号就是被定罪的理由;他们拒绝放弃基督徒的称号,这个顽固是要被惩罚的(p23)。图拉真的回信表明他基本同意普林尼的做法。
第二章主要讲罗马当时民间组织的性质和工作,存在行业公会、丧葬互助、以及敬拜神明的宗教社团。这些组织多有清楚的运作章程(p37-39),其会员有定期的聚会、聚餐、讨论,还有会员之间的互助机制。从一个角度,基督教会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类组织(p44),这也给基督教会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某些异教批评基督教会是非法结社、秘密结社(p45),因为基督教会为了避免逼迫,有时不得不秘密聚会。这种秘密的错误印象强化了异教的敌视,基督徒对此做出针对性的解释。
第三章讲的是罗马异教的信仰。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55?-117?)与普林尼约为同时代人,他对基督教的发展、甚至渗透到罗马,感到痛心疾首,他视基督教为“反社会”。与通常历史叙述不同,罗马异教并非仅是功利主义、形式主义,而是深深印刻在个人生活、社会运作的机制,并且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融为一体(p56)。罗马异教的宗教敬虔(pietas)意味着社会的凝聚力、社会正义、个人品德(p58),并为罗马共和的福祉和成功做出贡献(p59)。迷信/邪教(superstition)则不仅是非理性的,更重要的,它破坏上述的社会和谐、腐蚀个人品德(p61)。宗教从来不限于个人,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把社会制度、角色、以及个人和社会事件放在一个终极的框架里(p64),因为它是解读一切的框架。按照这个逻辑,罗马异教眼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是“反社会”、“反人类”的(p65)。米努修‧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批评基督徒,“你们不去看我们的演出,不参加我们的巡游,不到我们公众的宴会,你不参加我们神圣的运动会”(p66)。类似指控在几乎每个社会都有出现,例如清末民间敌视基督徒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样[6]。
第四章开始侧重于神学、哲学的质疑。盖伦对基督教不再是直接的轻蔑,他有基本的尊重,把基督教视作与其他宗教、哲学近似的学派,是罗马帝国内部诸多学派的一支(参见徒17:17-21)。罗马的宗教、哲学不只是理性层面的思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p76, 80)。盖伦对基督教的批评,是基督教的“无理性”,基督教的神的“随意性”,基督信仰不讲道理、不讲逻辑。在这里他抓住了基督教与异教的关键一点区别,神的创造、神与被造物的关系(p84-93),他不接受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异教也讲神的创造(不只罗马-希腊,各种异教都有),可异教的神是被造物的一部分,屈服于被造世界已有的规律,运用被造世界已经存在的物质;与之相对的,圣经启示的神是自有永有的、超越被造物的,在万有被造之前没有被造物,所以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这是盖伦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接受也不能想象一个不受制于自然和自然规律的神,“一切都能”、无所不能的神。这一点与近现代异教意识形态相同,他们不否定在世界里的神,他们否定的是在世界之上、在世界之先的神(罗11:36, 西1:15-17)。
第五章的主角是赛尔修斯。首先,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术士,就像异教的很多术士,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靠法术(参见太12:24)。接下来,作者列举了塞尔修斯的三个主要的神学批评,一是神子道成肉身,二是死里复活,三是基督的神性。塞尔修斯质疑:神是神,人是神,神不可能成为人,基督教的这个教导是“最可耻的”(因为这是对神的侮辱);如果耶稣是神道成肉身,那在这之前呢?神怎么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到人间?死人怎么复活?神怎么能逆反自然规律?基督徒把耶稣视作神来敬拜,如果耶稣是神的话,基督教还信仰独一的神吗?这不矛盾吗?这里作者提到异教的“独一神”的概念(106-108),异教并不彻底否定一般意义的独一神,异教可以接受在一个至高神之下的多神体制,即大神之下有很多次级神明,你可以敬拜这些小神,你敬拜他们就是在敬拜至高的神(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上帝”的概念类似)。但基督教不是如此,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是神子,与父同等、与父原为一(p120-121)。
接着,塞尔修斯针对圣经,尤其新约圣经关于耶稣记载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些记载来自道听途说,没有历史依据,使徒们或者是被蛊惑、或者是为了吸引人而制造了各种玄幻内容(与现代的圣经批评高度一致)。塞尔修斯还从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切入,耶稣和摩西的教导存在冲突时,是摩西错了还是耶稣错了?基督徒既然宣称敬拜的是犹太教(即旧约)的神,为什么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基督教的合法性何在?他继续批评基督徒不参与偶像敬拜、从社会中隔离(p118-120);还有基督教的年轻,才一百多年,而罗马、希腊、埃及的宗教,以及犹太教都已经数千年了(p121-123, 163);此外,基督教宣称的普世性也是荒谬的,历来都是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宗教,各民族有各民族的不同、各民族的传统,基督教的普世性是在破坏各民族的传统(p124-125)。
第六章波菲利的批评更趋近自由主义神学的观念。例如,他认为但以理书并非但以理在公元前六世纪所作的预言,而是公元前二世纪时他人伪托但以理之名写的,在书中所“预言”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写的(p137-143),这是典型的自由神学理论。他认为新约圣经的记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多有虚构、矛盾,尤其对旧约预言的引用和解释(p144-147)。他对耶稣的定位是伟人,在异教的神明体制的第三序列(p148):一是至高的神,二是次级的可见神明(如日、月),三是神化的伟人(这三重序列在其他异教、如中国异教也存在)。他还提到耶稣门徒对耶稣教导的异化,使徒们改变了耶稣的教导,耶稣并没有说自己是神,是使徒们把他变成了神、还要敬拜他(今天常见的观点,基督与使徒存在冲突,我信基督、不信使徒)。他继续了之前的主题,谈到基督信仰的社会毒害、无理性。最后,他回到塞尔修斯提到的,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信仰普世性、独一性,他有同样的质疑,“既然耶稣是救主,他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到人间,为什么隐藏那么久?”(p162, 其假定是神“欠”人一个救主);神既然是全人类的神,那就不应该只有一条道路,“通往如此神秘伟大的道路,不可能只有一条”(p163)。今天不信神的人质疑,不也是这些吗?
第七章是在基督教环境长大的异教徒尤利安。他对罗马异教非常敬虔、热衷,他在位的十九个月可以说是罗马异教对基督教最后一次体制性的攻击。他要求罗马的教育系统忠实于罗马异教的传统,抵制教育的基督教化;他利用当时基督教的异端,否定耶稣的神性。他批评基督教的启示是局限在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呼应塞尔修斯、波菲利,“如果他是所有人的神,所有人的创造者,他为什么忽略我们?”(p180-181)当然,使徒对此早有解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徒17:30-31)尤利安批评基督徒对待圣经记载过于死板,竟然把传说当作真实(p182, 关于创造);圣经的神是“愤怒的、记仇的、喜怒无常的”(p182-3);圣经关于创造的记载还不如柏拉图的记载全面(p183-4)。最后,他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异端,既然基督教自称取代了犹太教,他可以重建圣殿来打击基督教,当然,这个努力很快因为神降的灾祸而终止。
本书作者的立场是非基督徒学者的立场,虽然他比多数这类学者更为客观和中立,他认识到异教与基督教的复杂互动,但把基督教、基督教神学仅仅视作这个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我们能注意到这个缺陷,书中呈现的历史风貌和脉络,对我们理解教会历史、属神信仰与异教的互动,是有益的,并且这不局限于罗马异教、也不局限于古代。异教对属神信仰的批评,始终是围绕着几个核心主题,从古至今没有变,因为圣经没有改变,罪人也没有改变。
[1]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Secon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其叔父为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是罗马的作家、博物学家、政治家,著有《自然史》,23-79 AD,于公元79年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去世。
[3] Bithynia,参见徒16:7, 彼前1:1,黑海南岸,今天土耳其北部。
[4] Trajan, 53-117 AD, 98-117年在位。
[5] 中国元、明、清对此都有控制,清代尤其严格,如明伦堂的《卧碑文》明确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
[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266.html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自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