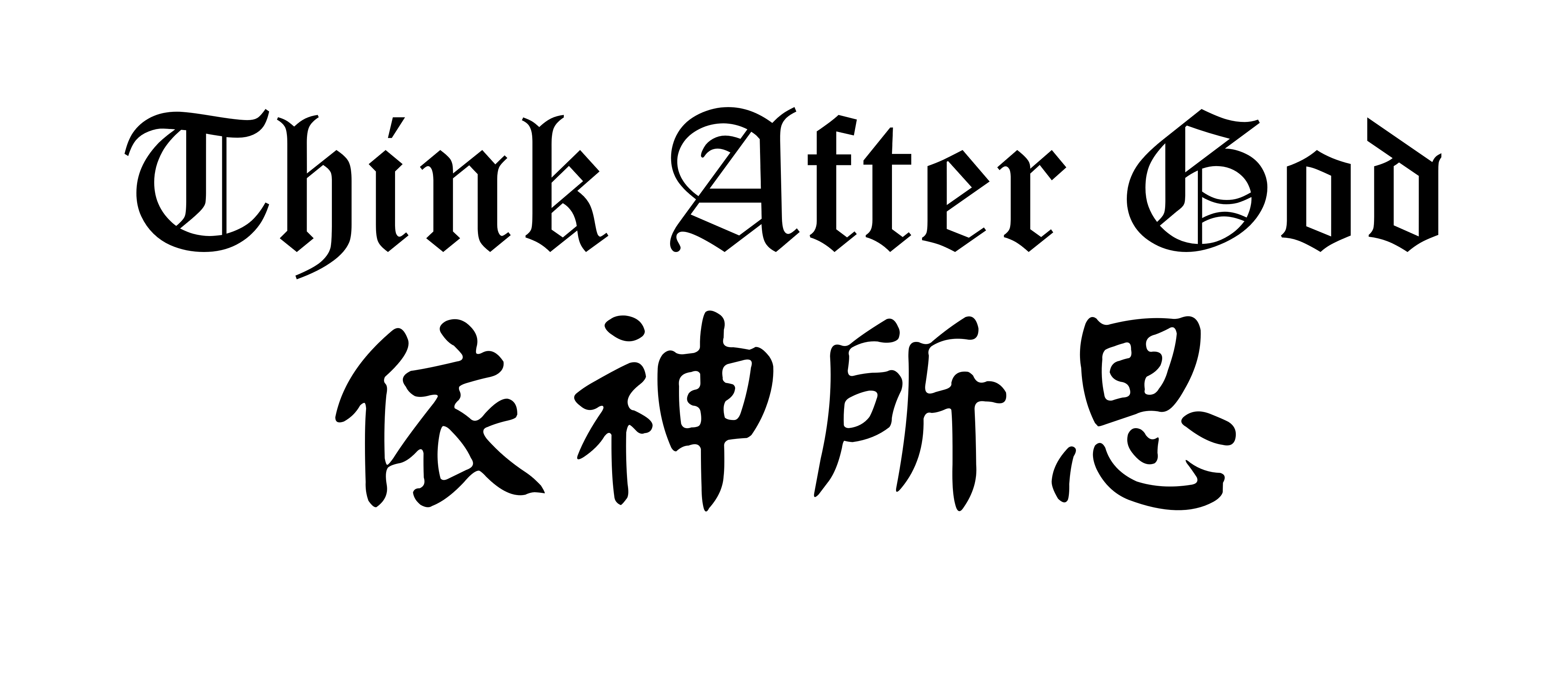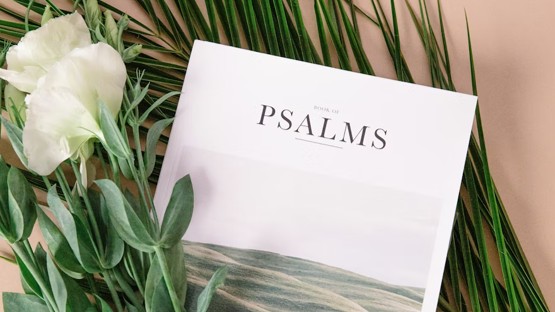诗人讲排斥、远离恶人,不局限于大卫、不局限于旧约,这是不变的属神原则,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仍然重要。首先,诗人排斥、远离恶人,是排斥、远离恶人代表的罪恶生活状态,诗人不认同这种状态,以至于厌恶、憎恶。其重点不是隔离的形式,例如“不站罪人的道路”说的不是人实际走的道路,指的是不认同罪人生命的走向;“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讲的不是座位本身,指的是不认同罪人生命的选择,不仅不认同,还相当排斥。这是属神的人应有的态度,善与恶是相互排斥的,义与罪是相互排斥的,向往前者必然排斥后者,既然是义人、是属神的人,那就一定要、也一定会排斥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在两个相互排斥的选择面前,我们的选择只能有一个,选择这一个就意味着排斥另外一个。不可能说我们渴慕神、但不排斥罪,不可能说我们事奉神、但不远离罪,不可能说我们对圣洁深情款款,又对罪恶暗送秋波。我们如果不排斥恶人行走的道路,那就没有在意义人行走的道路,我们也不会屑于行走这个道路。使徒讲,“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厌恶恶与亲近善是一个决定、一种状态的两个方面。我们经常空洞的谈敬虔、圣洁,好像我们可以在对罪、对恶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对圣洁、敬虔可以大有作为,这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是痴人说梦。如果罪不值得我们厌恶,那我们对圣洁的向往是空的;如果罪人的生活状态不值得我们排斥,那我们对敬虔生活的理想也是空的。
我们信神,不是在原来的状态上添加了信神、顺服神,圣经讲的信包括悔改、转向,包括目标和好恶的转向,判断何为美好、何为丑恶,何为幸福、何为灾祸的转向。远离罪的前提是排斥罪、厌恶罪。假如内心的好恶不变,再强的意志力、执行力也是在做无用功。“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属神的人要远离、排斥得救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些事情“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有些人说,那你排斥、厌恶你自己的罪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说别人?别人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做你的好事,排斥别人做什么?我们要清楚诗人和使徒讲的排斥,到底排斥的是什么。是罪,当然包括自己的罪,但绝不仅限于自己的罪,使徒说的是“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里讲的是属罪的生命,不敬畏神、不信靠神的生命状态。所以,诗人和使徒强调的都是属神与属罪、义人与恶人的区别,也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排斥。这种排斥不源自人际关系,诗人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他对某个人的态度,与这个人对神的态度是相关的,他与这个人的关系,与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是相关的。最终是因为神排斥恶人,所以他排斥恶人;因为神厌恶恶人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也厌恶恶人的生活状态。箴言讲“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诗篇讲“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新约讲“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属神的人应爱神之所爱、恨神之所恨,与神同好恶,才是与神同行。
其二,诗人排斥,远离恶人,不只在态度上,这一定以某种方式表现在人际交往。上述对罪恶生活方式的排斥,不可能不涉及到在罪恶中生活的人。有些人经常想要把罪和罪人分开,对罪是一种态度、对罪人是另一种态度;这是不可能的,罪无法与犯罪的人割裂开,说到罪一定要谈到犯罪的人,不存在神排斥罪、而不排斥犯这个罪的人,因为就是这个人在犯这个罪。所以属神的人对罪恶生活方式的排斥,一定会体现在罪恶中生活的那些人的排斥;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你愿意接近的,那这些人也是你不愿意接近的。这不是一刀切的断绝与非基督徒的交往,但这同样不表示基督徒像得救之前那么交往,不表示基督徒像非基督徒一样交往,基督徒与人交往受神的话语节制,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人觉得基督徒什么时候都应该接纳人,不论什么情况都笑脸相迎,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必须停止与某些人的交往、停止某种性质的交往,例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新约教导的排斥、远离,不只是心理上的,也是行动上的,与诗篇是一致的。
圣经还有关于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每个人的人际交往都是有选择性的,与人交往始终是有取有舍,下面看几种情况。其一,如果与某人的交往是犯罪,是对犯罪的直接认同或参与,这是禁止的。例如某些人邀请基督徒参加异教敬拜、参与道德败坏,我们应当远离这些活动,如果需要的话,远离这些人。“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不是随意的事情,不是什么出于礼貌、不想推辞的事情,使徒警告我们,“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其二,如果与人的某些交往,虽然不直接让我们犯罪,会引诱、胁迫我们犯罪,这种交往是我们应当慎重、警惕,保持距离的。“滥交是败坏善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做伴的必受亏损”,“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诗人远离恶人,是清醒的自我保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不希望在其中沾染,被罪恶引诱,被罪恶的群体掳获。某些人际交往,不仅是浪费时间,且是败坏生命。我们不应该有精神洁癖,好像与其他人一接触,自己就不洁净了、就被引诱了,可我们应该有基本的精神洁净,知道什么是污秽、什么会污秽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自己容易在什么诱惑面前倒下。其三,与人交往是基督徒的见证。与人交往是社会活动,也是被社会解读的活动,两个人共同出现在某个场合会被人解读为二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人类认知判断的基本规律。与某些人的某种交往,即便是交往本身没有犯罪,对于基督徒的见证也可能是污点,例如圣经要求教会的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说到这里,有人说,那这不还是法利赛人吗?洁身自好、沽名钓誉,这就说到第三点,诗人排斥、远离恶人,不论是态度还是行动,都与法利赛人不同。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很容易与法利赛人混淆,例如法利赛人批评主不应该“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不应该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种批评对吗?主是否违背诗人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当然是否定的。其一,主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不表示主认同他们的罪,圣洁的主对罪的态度始终是清楚的,让他们认罪、悔罪、得以赦罪的,主从来没有模糊这一点。其次,主的使命是“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主到罪人中间,与罪人接触、传讲神国的福音;类似的,主给基督徒的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与世人保持互动,传讲基督的福音。其三,主与罪人互动、让使徒与罪人的互动,不是没有选择性的,其中也有排斥、远离,例如,主始终与犹太的宗教精英保持距离,有时有意避开某些人、某些城,教导门徒“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所以,主的教导与诗篇没有矛盾。法利赛人不是因为在持守旧约教导,所以批评主,而是他们不明白旧约,在误解、误用旧约。
诗人的义不是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诗人与恶人的区隔也不是自命清高,不是出于骄傲。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法利赛人的排斥,不是诗人讲的排斥?为什么法利赛人排斥罪人就是错的,诗人排斥罪人就是对的?说到排斥,每个人都有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人,这个排斥很容易变异为,就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排斥,变成自我的、狭隘的排斥,发自私欲、罪恶的排斥,这也是法利赛人的排斥。诗人则非如此,如前所述,诗人的好恶是效法神的好恶,是出于神与人的关系,“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诗人的情感、反应不出于私欲、私心,这种恨恶、排斥是正的,不是邪的,因为这来自神、受神节制。这也联系到之前讲的敬畏神,是公还是私、是正还是邪,很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敬畏神,只有敬畏神才不会是私心、不会是邪道,只有敬畏神才能除去人里面私欲的冲动,才不会自以为义、自命清高。否则变成法利赛人是很自然的,既然我是义人、别人是恶人,私欲的本能是居高临下的鄙视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以抬高自己,用神的名义伪装私欲的好恶,把我个人不喜欢的都当作神的敌人,把我对别人的恨当作神对别人的恨。这个秩序是颠倒的,诗人讲的是把神的仇敌视作自己的仇敌,而私欲讲的是把自己的仇敌划做神的仇敌,把自己的私愤当作是神的愤怒,把自己的骄傲当作是神的公义。这是人的内心很容易发生的转变,也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事情,瞄准的是诗人的状态,实际是法利赛人的状态,不知不觉之间,私欲已经悄然显现,劫持了我们的判断、情感、反应。没有真正的对神的敬畏,空讲远离恶人、排斥恶事,一定会成为法利赛人的样子,甚至还不如他们,因为没有对神的敬畏,就是我站在神的位置上,妄称神的名对人宣判。
也是因为敬畏神,诗人排斥、远离恶人的时候,没有只盯着义人与恶人的区隔,而忽视圣经关于神、义人、罪人的完整图景。他不因自己是义人而骄:他知道义人之“义”是神的恩赐,不论是得救的义还是得救生命的义都是神的恩赐,因为义人仍然犯罪,仍然需要认罪、悔罪,处置罪、去除罪。他不因别人是罪人而暴:恶人现在藐视神、敌挡神,在神的愤怒之下,可这并不否定神对他们还有恩典,他们可以悔改、信靠神。“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人清楚的区隔义人与恶人,远离、排斥恶人,但他并没有只看到这个区分,他还意识到,罪是在每个人心里的,属神的人对罪并不免疫,属神的人不垄断神的恩典。所以,诗篇不仅提到排斥罪人,也提到教导罪人、呼召罪人悔改,“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属神的人与人交往,是效法神的好恶,效法神对这个人的态度,我们的效法不是狭隘、片面的模仿,而是全面的效法。神对他有愤怒、我们也应有愤怒,神对他有排斥、我们也应有排斥,神对他有恩慈、我们也应有恩慈,神对他有忍耐、我们也应有忍耐,神呼召他悔改、我们也应呼召他悔改。仅仅模仿其中的一点,只有排斥、只有接纳,这很容易,但这不是效法神。这些态度在神里没有矛盾,在我们这里也不应有矛盾。
以上摘录自《圣经概览》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