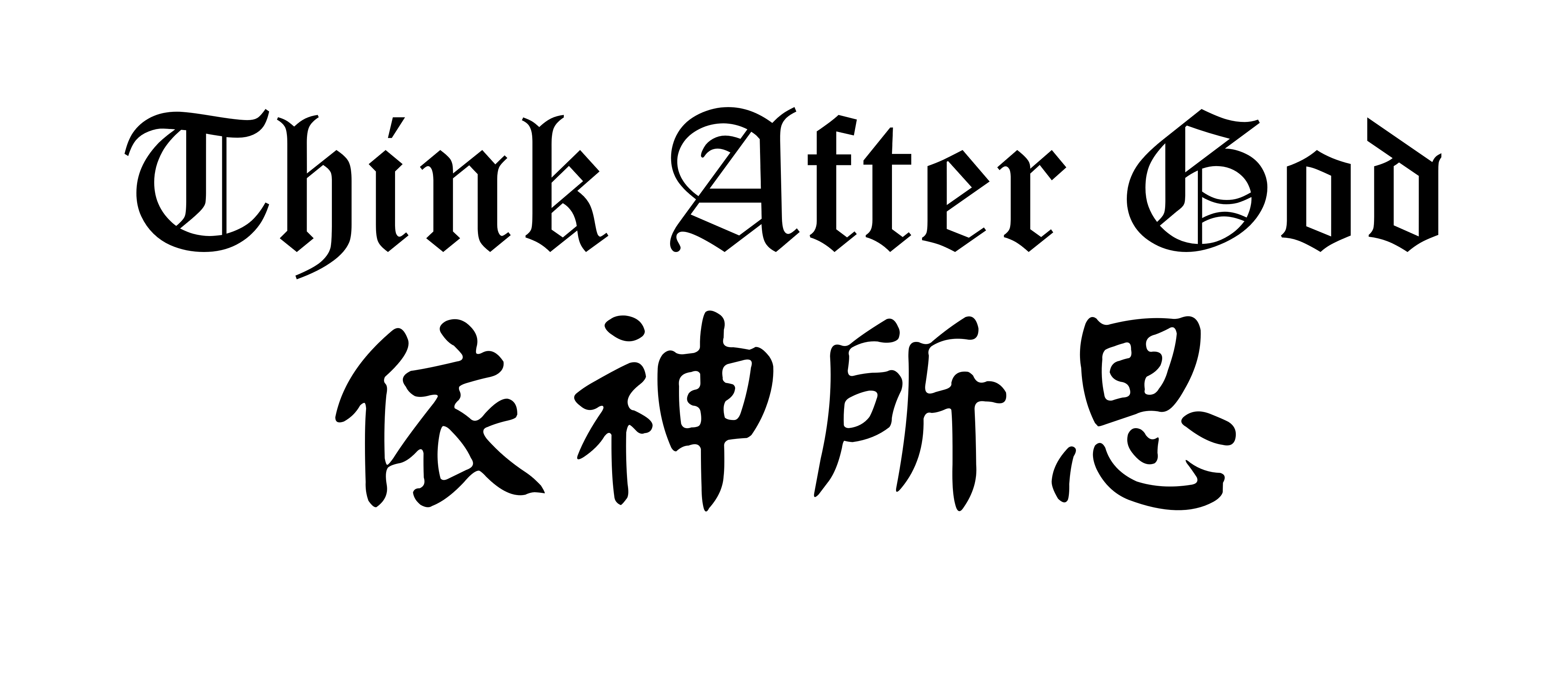之前我们谈过万历、雍正时期基督教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这里就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政治,谈一些原则问题。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是无法回避政治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会是政治组织、不是因为基督徒有政治野心,而是这个世界是政治化的世界。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约17:15),这个万民是在各种政治框架里组织的万民,这个世界、尤其是今天的世界不仅是政治化的,而且是泛政治化的。不仅仅是在非基督教的地区,无神论主导、伊斯兰教主导、佛教印度教主导的社会,而且是在后基督教的社会,如欧洲、北美。政治与基督徒、基督教的关系,不是今天基督徒、今天的某些基督徒才思考的问题,这是历代基督徒、历代属神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等这些旧约圣徒遇到过,主和使徒们也遇到过。主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13:1-7)。属神信仰从性质上讲是超然于政治、超然于世界,从运作上讲不可能超脱政治、超脱世界。一个基督徒说自己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等于在说自己和世界没有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你可能没有投票权,你可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或恩赐,但作为基督徒,你与政治有关系,神的教导和诫命包括关于政治的内容。更重要的,神清楚的定义了神的权柄与人的权柄(包括政治权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是神给的,一方面,他们的权柄是在神之下的,当他们的要求与神的诫命冲突时,基督徒的选择只能是违背人的要求、顺服神的诫命。
这是属神信仰、基督教、基督徒与政治的冲突的主要来源,不是基督徒寻求宗教的政治化[1](当然这存在),而是异教寻求政治的宗教化,是政治权柄不愿意停留在神设定的界限内(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认识神),政治进入了宗教,或者政治变成了宗教。这不是现代才有的,例如,但以理等人所在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神设立的王,“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但2:37),但以理可以作为官长、犹太人可以作为臣民为尼布甲尼撒服务,顺服他的命令。但在两件事情上但以理没有服从,一是王给他们的异教食物,他拒绝接受,因为这违背神的诫命(但1:5-16);二是王只允许民众向王祈求,但以理同样拒绝,因为这还是违背神的诫命(但6:1-18, 另有其他三人拒绝敬拜金像,3:1-15)。是但以理的立场变了吗?是但以理的忠诚变了吗?是但以理把宗教政治化吗?不,是尼布甲尼撒把政治宗教化,他要进入宗教领域,要成为人敬拜、祈祷的对象。使徒教会、初代教会时期的罗马,是一样的,基督徒与罗马政府的冲突,核心是罗马要求基督徒敬拜凯撒,称凯撒为主。
说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从晚明清初直至现在,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毋庸多言。在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着强烈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督教与政治的互动、碰撞不可避免,基督教的公开活动空间基本是政治决定的。中国政治与巴比伦、罗马的不同之处,其中一点在于,它并不是带着直接的、显明的宗教意味,因为表面上看,它没有一个官方的宗教,也没有在推行官方宗教,儒家可以被视作非宗教的伦理学说,更不要说今天的无神论。但这不表示政治是远离宗教的,更不表示政治不关心宗教,这只能说明在这个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中国的政治宗教化与罗马的政治宗教化是不同的形态,这是理解基督教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点。
罗马的政治宗教化是官方宗教,所以与基督教的冲突是有神论之间的冲突,应该敬拜哪个神,更准确的讲,是多神论与一神论的冲突,罗马允许敬拜多个神,但基督教只允许敬拜一个、且只是耶稣基督启示的神。中国的政治宗教化是官方的非宗教,所以与基督教的冲突在形式上是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冲突,明朝如此、清朝如此,民国、今天仍然如此。我们说的“在形式上是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冲突”,只是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对于明清儒家、民国和现代知识分子,即在中国社会占据意识形态主流的人,基督教的问题不在于基督徒信的神错了,应该信另外一个,而是基督徒信神本身就是“荒诞不经”(明沈㴶),“诞幻无稽之谈”(雍正《圣谕广训》)。有人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反对信佛、信道?为什么单单反对信基督教?从一个角度,他们也反对(基督教多被与佛、道的邪教并列,如白莲教、闻香教),但更重要的,在他们眼里,佛、道远没有基督教“荒诞”,基督教的“荒诞”在于它是严肃的有神论,且尝试维持这种严肃的有神论。严肃的宗教(佛、道也不例外)在主流意识形态是被边缘化的,不同的是,佛、道是被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驯化”的(即没有明显违背主流的宗教意识,见下),不是主流、但对主流也没有什么威胁,但基督教尚未被“驯化”,或者不愿意被驯化。
主流的无神意识形态(传统的儒家也好,现代的无神论也好)并非彻底的非宗教化,而是一种隐形的宗教,他并不直接承认这是宗教,因为这是以道德、传统、政治作为包装的宗教,这是宗教,但他不认为这是。这一点对认识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关系很关键。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康熙时期,传教士与康熙等人在祭祖、祭孔等仪式上的争论。康熙等[2]认为祭祖、祭孔不是宗教,是道德的表达,是敬天敬人、慎终追远。为什么他不认为这是宗教?不是因为这不是宗教,而是因为这些仪式已经渗透到多数人的意识,他不把它当作宗教了(这是潜意识的宗教),他觉得你只有到庙里拜佛才是宗教(这是有意识的宗教)。类似的,今天的丧葬礼仪(以及某些婚姻礼仪),如烧纸、烧香,你问多数人,这是宗教吗?他会否认,他觉得这是传统、更是道德,你不做这些事情就是不道德、不孝,你的宗教也是不道德、不孝。然而,如果祭祖、祭孔、烧纸、烧香没有宗教意味,只是表达尊敬的话,有必要有这些仪式吗?如果人死后就是结束,什么都没有,这些仪式又是在做什么?这不只是民间的,民间是传统、道德包装的宗教,官方是政治包装的宗教,无神论并非彻彻底底的无神论,它对自己的表述和宣传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例如,一方面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歌词),一方面说某某是救星,其他宣传术语想必不用多说。
除了基督教与这个隐形宗教的冲突,还有一种冲突是更直接的,那就是基督教与政治权力的冲突,这与罗马社会是类似的。康熙、雍正等限制基督教,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考量,但他们的自我定位首先不是儒家的卫道士,而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与罗马的皇帝一样,对皇权的定位是绝对皇权,不可能有什么是皇帝管不了的、不能管的。这与基督信仰的冲突是,他们认定的绝对皇权与圣经定义的有限皇权之间的冲突,世俗的无限政治权力与圣经定义的有限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中国相比罗马的问题更甚,因为中国有着罗马没有的中央集权。所以,中国的政治宗教化的基本认识是,政治对宗教有着绝对的主权,政治理所应当的延伸到宗教领域,任何宗教的信徒都应该服从政治权力,唯命是从,这种认识是公理。这在定义上就与圣经是相悖的,圣经教导基督徒服从执政掌权者,但这始终是有条件的,有底线的,如果人要求的是悖逆神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不是某个朝代、政党,某个皇帝、领袖的问题,这是在根本定义上的冲突,绝对和有限之间的冲突,没有底线和有底线的冲突,这是任何政策的改变无法弥合的。
从这个层面看,从晚明到今天,这个基本冲突并没有改变,雍正的所谓苛严是在这个框架下,康熙的所谓开明也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友好、敌意都没有超越这个框架。基督教在形式上的大发展时期,多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的弱势时期,其原因也是如此,这也造成了基督教的多次起起伏伏。
延伸阅读:
[1] 在教会历史的部分阶段和部分地区,部分基督徒尝试通过政治手段推广基督教进而实现并维持基督教的社会化。宗教政治化不是指基督徒在其所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内设法推动与基督信仰一致的道德、法律、政治秩序,这是正确的、也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例如一个基督徒的法官应该坚持正义、不偏不倚,一个基督徒的议员应该否决那些将罪恶合法化的动议;这种合理的参与不同于把宗教政治化,把宗教政治化首先混淆了宗教和政治,混淆了主上面说的“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混淆了道德与信仰、行为与拯救、教会与社会。这以后展开谈。
[2] 包括部分受传统儒家影响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