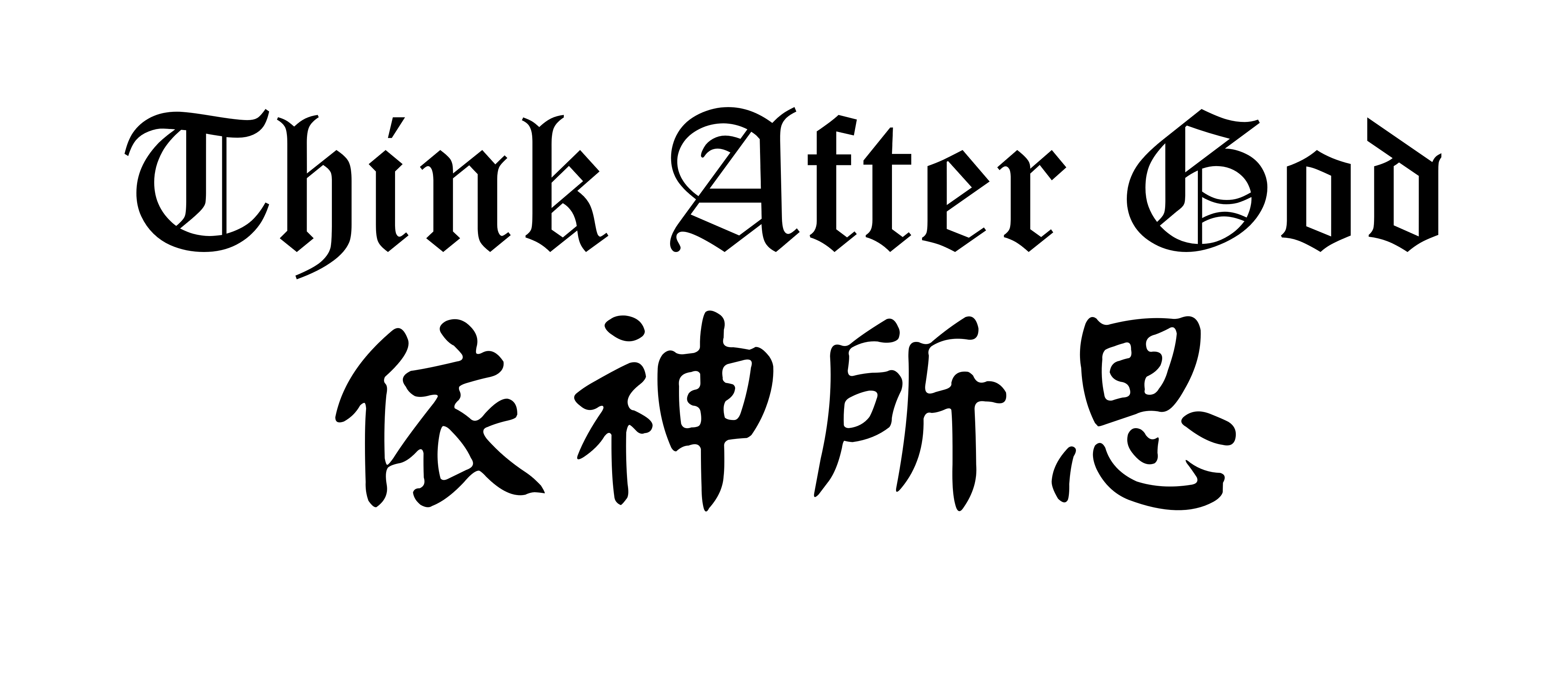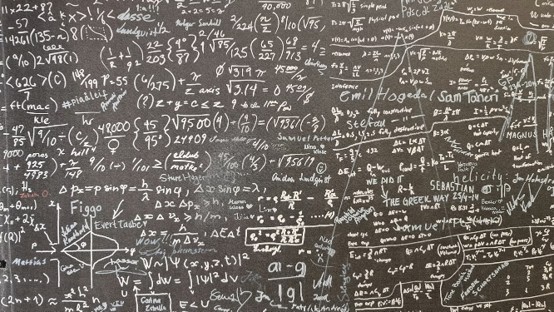喜怒哀乐,愤怒是人最常见的情绪之一,可能深藏于内、可能表露于外,可能暂时、可能长久,可能看似激烈、可能看似温和。愤怒不见得一定是罪,公义圣洁的神有愤怒(罗1:18, 2:5),公义圣洁的主有愤怒(约2:15-16),先知和使徒们有公义之怒(出32:19-20, 加5:7-12),但人的愤怒经常是罪,或者说经常容易异化为罪[1],这是神在圣经里多次告诫的——愤怒的罪。
罪的定义
旧约,尤其智慧书,大量提到愤怒、易怒的罪,“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暴怒的人必受刑罚”,“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诗37:8, 箴14:29, 15:1, 16:32, 17:27, 19:11, 19, 22:24-25, 25:28, 29:11, 传7:9)。愤怒的罪,与性情暴躁、没有自制力、作恶、刑罚、愚蠢联系在一起,不是神喜悦的,是人际关系的毒药。
在新约,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太5:22);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其中多处与愤怒直接相关。使徒教导,“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西3:8, 亦见加5:19-21, 弗4:31)是悖逆之子所行的,基督徒应当弃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弗4:26-27);“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1:19-20)。愤怒“并不成就神的义”,是魔鬼试探人犯更大的罪的切入点,往往导致更严重的罪(亦见雅3:6)。愤怒的罪,与属神的身份、基督的福音不相称:有愤怒的罪就没有爱,“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4-7),愤怒之罪是出于嫉妒、自夸、张狂,做后来自觉耻辱的事情,求自己的益处,是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自己的不义,不包容人、不信靠神、不盼望神、没有忍耐;有愤怒的罪,就没有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23),毋庸多言,愤怒与这每一项都抵触。另一方面,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之一,是“有节制,自守,……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提前3:2-3),“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 (多1:7),这是教会领袖的基本品格。
那我们如何对待愤怒的罪?
罪的忽视
首先不是如何对待这个罪,是如何重视这个罪,再往前问,是为什么轻视这个罪。愤怒的罪,容易被轻视,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一,不义之怒经常被我们用公义之怒的名义掩盖,因为愤怒不见得是犯罪,神也愤怒,有些事情的确值得愤怒,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把愤怒的罪正常化的理由,天经地义的理由:“难道某某不值得愤怒吗?难道这正常吗?”“只要不正常,只要不符合圣经教导或者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就值得愤怒,就可以愤怒,就是公义之怒。”这种逻辑看似没有问题,然而大有问题,且不说我们所谓的理想状态可能并不符合圣经教导,就算是圣经的教导,愤怒就是唯一正确的回应吗?当然不是,神不是如此,主不是如此,先知和使徒不是如此,神是“不轻易发怒”(出34:6),主甘愿受辱、为杀死他的人祷告(路22:63-65, 23:28-34),摩西受人毁谤、没有愤而回击(民12:1-3, 14:5),使徒牧养基督徒是如父如母的心肠(帖前2:4, 11)。我们轻易发怒、事事发怒,只有一点不满意的理由就发怒,反过来安慰自己说自己是公义之怒,这是自我欺骗。
其二,除了上述的迷惑性,不义之怒被忽视,还因为它在人看来过于“普通”,而后果往往比较“轻微”。“谁又不会愤怒呢?谁能彻底避免愤怒呢?更何况,我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就算犯了大错,一时冲动,也是孤立事件,以后注意就好。”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一时冲动”的犯罪,是我心里面的愤怒突然爆发、不受控制,然后伤害到人、伤害到自己、冒犯了神,这是我们会反省的,但这可能也是我们唯一会反省的。在这个“一时冲动”之下涌动的岩浆,我们不重视、别人也不察觉。我们并不彻底无视愤怒的罪,但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做的是控制、甚至公关,如何控制这个罪不冲动的爆发,如何不让它爆发后造成严重后果。而深藏于下的源头,被长久忽视,且在长久恶化,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严重的扭曲了人心、人际关系、神人关系。即便这样,我们可能还是继续用上述“公义之怒”、“正当之怒”的借口掩盖,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敬虔,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能自拔。这种易怒、偏激,使得他的状态,尤其是与人相处的状态,比不信神的人还要差,他比不信神的人还要自我,因为他的借口比不信神的人还要正当。
罪的表现
我们先从罪在意识、心理、情绪的层面看愤怒之罪的逻辑。愤怒是源于不满意,愤怒的罪是因何而不满意呢?这里且不说那些直接与犯罪相关的,即因不能直接作恶而不满意,这里针对那些并不与直接作恶相关的事情,也是更常见、更隐蔽的罪,即某些人事物的确存在问题,至少是看似存在问题。愤怒的罪在于,没有在属神体系里正确看待、对待这些现状,把不是问题的当作问题,把小问题当作大问题,把应当以其他方式对待的,全都以愤怒对待。这背后的机制,其一,是对现实整体的不现实期待,空洞的理想主义,这个理想可能是自我构想的、也可能是来自圣经的。如果是来自圣经的,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并不错,基督徒应当追求完全(太5:48),“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3:13-14);他的错误在于,把这个完全的理想,僵硬的、机械的、自以为是的套用在现实。问题不是有这个理想,而是只有这个理想,不顾现实的只盯着这个理想。这样的人是顽强的,顽强的坚持,顽强的拒绝妥协,可这种顽强随时可能异化为顽固,甚至冥顽不灵。
其二,这种不现实的期待,会体现在多个方面,简而言之是悲观、苛责,对于挫败、失望的低容忍度,于己于人皆是如此。这开始于自己,他对自己的不现实期待,导致对自己的整体悲观判断,这种悲观一方面导致他彻底放弃某些事情,一方面导致他更迫切的投入某些事情。不论是放弃还是继续,他的悲观是继续的,因为放弃了,他自视做不到,这让他悲观;没有放弃,他自视做不好,这也让他悲观。这在人心里会产生多种反应,例如羞耻、耻辱、畏缩,因此而有的自我隔离、封闭,还有是给予自己更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是提高强度进行更大投入。这个压力的结果是什么?是他的生活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因为他希望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个在有限时间实际不可能的目标。他想做的事情,他焦虑没有做得够好、没有做得够多;他不想做的事情,他觉得是干扰,如平常琐事,是不得不做的,必须以最小的投入、最快的时间完成,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他的效率背后可能是焦虑。这种情况下,易怒是焦虑的自然产物,对自己的愤怒、对周围干扰的愤怒,这样的人无法真正的享受美好,所有的美好都被焦虑笼罩,在短暂美好之后、之下是深深的焦虑。
由于这个顽固的不现实的期待,他对现实的整体看法是悲观的,甚至是对抗的,所以他会注意世界的敌意,并经常放大世界的敌意。当然,不是说世界不存在对抗、人间没有敌意,但这里讲的是被人为放大、甚至是自己臆想的敌意,而且是被纠缠、无法放下的敌意。这个敌意带来的危机感也会随时导致愤怒,易怒,会把所有信号放大,从最坏的情况评估现状,从最大的恶意揣测人。对人、对己的两种路径是相互影响的,对人的悲观、苛责会强化上述的自我认知,强化自我隔离,对己的压力、焦虑会强化这里对人的敌意(因为干扰),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罪的剖析
既然是罪,就不只是意识、心理、情绪的问题,不只是于人于己的问题,不只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问题,根本上在于神人关系,人在属神认知、品格的缺失和错位。其一,这种不现实的期待,偏离神的教导。有一种满足现状是罪,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是罪,没有理想是罪,过于理想也是罪。不现实的期待,就认知而言,是偏激的,因为他只关注圣经教导的理想,不愿正视圣经教导的现实,只看到理想的清晰,没有意识到现实的混沌、不可解。过度乐观是片面的,过度悲观也是片面的;看不到敌意是错,放大敌意也是错;没有距离感是错,保持距离导致隔离也是错;看不到不正常是错,只看到不正常也是错。没有按照神的启示和工作看待世界,不论是偏离到哪个方向,都是错的,也都会导致罪。他往往只看到罪在工作,没有认真的看神的恩典在工作,只看到是人的罪让某件事情发生,没有思想最终是神的旨意让某件事情发生,只看到人的敌意,没有想到神的美意(罗8:28),如此的认识不仅是偏激的,也是无视神。
其二,这种不现实的期待,背后存在骄傲,甚至可以说显著的是骄傲。还是前面提到的关系,没有理想、满足现状的人是骄傲,但过于理想、苛责现状的人同样是骄傲,在前一种骄傲和后一种骄傲之间是谦卑,两种骄傲看似距离遥远,谦卑和骄傲却在一线之间。过于理想、苛责现状,其实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可以达到某种状态,认为自己必须被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当然最重要的,是幻想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拒绝认真严肃的面对神给予自己的状态和环境,这是骄傲导致的悖逆。按照神的诫命严格对待自己、他人,与苛责自己、他人,其界限并不容易看到,前者的严格是在顺服神,后者的苛责是在苛责神,前者是谦卑,后者是骄傲。
对神的苛责,虽然可能不会直接表现在对神的埋怨,但会表现在对神缺乏感恩,因为这样的人始终处于焦虑、不满足,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认真的思想神在现状之中给予他的现实的恩典,包括在平常琐事的恩典。他有对现状的不满足,可没有在现状的满足,而“知足”是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品格,“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靠主大大地喜乐,……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林后12:9-10, 腓4:4, 11-13, 提前6:6-10, 来13:5)。没有这个知足,就没有平安、喜乐、感恩,在遇到挫败的时候就没有忍耐,没有平安、喜乐、感恩就会焦虑,没有忍耐就会易怒。
而这些是没有信靠神的结果,焦虑源自不安全感,焦虑是自尊、自我价值的搏斗,汲汲于某种目标,是汲汲于这个目标带来的东西,是不能接受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后果,所以从才会焦躁的穿梭在一个一个目标,快速的放下这个、拿起那个。属神的平安、喜乐,不是懒惰、散漫,可也不是焦虑,属神的、信靠神的没有上述的焦虑,因为他的自尊、自我价值不取决于某种现实目标,而取决于基督。出于信靠神、信靠神在基督里的应许、信靠基督通过圣灵真实的同在、信靠神对现实的真实的掌管、信靠神在现实里真实的美好旨意,属神的人可以忍耐,可以接受非理想化的状态,甚至可以接受极端恶劣的状态,不是说这些不理想的就幻化为理想,而是不论有多么不理想,不论有多么恶劣,属神的美好仍然真实,仍然与我们同行,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品味、感恩,仍然足以让我们在其中平安、喜乐,仍然足以让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 如摩西,民20:7-13, 亦见申3:26;如雅各、约翰,路9:54-56,在此提到的以利亚并犯罪,但雅各、约翰犯罪。